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山西篇) 我们曾经年轻(1)
本报特约撰稿人:董丰
导读:为纪念中国知青运动五十周年,由《中国知青文库》编委会(以武汉大学出版社为主)、文化部《文化大视野》编委会、香港中华知青作家学会、中国青年作家学会、北京绿茵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赞助方)共同举办的“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活动从2018年8月开始,历史一年的时间在2019年9月初终于揭晓。评委会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三千多份知青作者(其中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503人)来稿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和评定,最后评选出一等奖作品145篇,二等奖作品112篇,三等奖作品113篇。”获奖作品共370篇,全部编入《永远的知青》——中国知青作家杯优秀作品选集中,共四卷137万字。本报特约撰稿人董丰的作品荣获一等奖。
现在很多七零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并不了解中国知青这个群体当年的真实的生存状况,因为诸方面原因,官方对这段历史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价也不是很多。但如果你从头至尾翻阅一下这四部《永远的知青》,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中国知青。
从牧区到农区——罗庄印象
1968年7月我从北京到内蒙锡林格勒盟牧区插队,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时至1970年秋,患肝炎在北京治疗了几个月之后我的黄疸指数和转氨酶终于趋于正常,到了返回草原的时候了。但是生病伤了元气,原来紧致的人体虚发了一圈儿,蒙古高原的严冬将至,估计一时半会儿身体难以适应。
我的姐姐董盈是中学5年制实验班的67届毕业生,1968年年底和一帮同学到雁北插队。那里虽然是盐碱地,穷得叮当响,但是毕竟是内地,气候好一些。同村知青杨百揆把县知青办接收我的批文办了下来,于是我借坡下驴,年底前到内蒙办妥了手续,转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罗庄插队。
因为不是从学校直接分配到山西插队的,所以我的名字没有在县知青的花名册里,但是在罗庄插队的短暂生活帮助我了解了当年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仍然是一段珍贵的经历。
第一次踏上罗庄的土地是1970年夏天,那是我在内蒙插队两年后回北京探亲,中途转道山西看望姐姐。初到访,我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里的知青没有社会上流行的痞子气,很理性、知性、成熟,至少说话里不带有令听者难堪的脏字,像是一股清流。罗庄的女知青都是我中学甚至小学的校友,她们乐观清纯,文雅自律,保持了很多书生气,相比牧区知青更有集体感,这也是罗庄吸引我的原因。
我们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文革前是北京最好的女校,北京四中是最好的男校。文革中学习好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而作为“修正主义”学校的学生在插队时必然要被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女附中和四中学生在山西的插队地点就是雁北地区最贫穷的山阴县。罗庄的知青组最初有十一个男生,十个女生。我到罗庄时人员开始松动,陆续有人离开。
从牧区转到农村插队,我感觉有得有失。牧区虽然自然条件恶劣,生活环境原始,但是畜牧业的产出是马、牛、羊、骆驼,每年大队的收入不错,一人一天的工分值接近一元。牧区放牧工作的工分计算以畜群为准,男女同工同酬,知识青年经济上可以完全独立,至少衣食不愁。
罗庄位于雁北桑干河畔的盐碱地区,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村里一个男劳力一天记10分工,工分值8分钱。女劳力一天记8分工,每天能挣6分4厘。知青第一年下乡,国家供应528斤带皮粮,以后就和农民一起挣工分、分粮食。一般的小队每人分三百多斤带皮粮,少的只有二百七八十斤。辛苦一年下来,不少人挣的工分不但不够分到的口粮钱,还欠队里的账。即便有余款,队里也只给你写一个欠条。所以知青在经济上根本无法自立。
当时雁北的农业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农活基本靠人力。谷物脱粒靠人扑打,用的是战国时期就有的农具连枷。庄稼地的平地用人拉石头磙子完成。脚踩在翻耕过的松软土地上,拉着石头磙子一天走下来膝关节酸痛。除了农忙抢种抢收,雁北的女人结了婚就不下地干活了。女知青初到农村,拉石磙子平地,和男人一样一干就是一天。比起牧区的骑马放牛,农村的劳动强度更大、更辛苦。
内蒙牧区生活环境比较原始。蒙古包后面就是天然厕所,浩特(畜群组住地)里的狗很快会把粪便清理得干干净净。在罗庄我们有了男女厕所,多了隐私保护,但是初见一个将近一人深、两米多直径的大粪坑还是让人生畏。人要蹲在石头砌的坑沿儿上脸朝外便溺。坑里要经常填土,以便以后起粪时人能下到坑里把粪土铲出来做农田肥料。
我印象里的猪都是肥头大耳,好吃懒做,在猪圈里踩着烂泥晒太阳。这里农民自家吃不饱,养的猪经常放养在外吃百草,一个个精瘦灵活。它们时常闯进厕所,跳下粪坑拱食,再利索地蹿上来。我初来乍到感到惊奇,立马对猪的形象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
知青食堂里有大队的一个妇女给大家做饭。我们的主食顿顿是玉米发糕,副食是胡萝卜和土豆丝泡成的一大缸窝酸菜,很少有荤腥。粮食不多,顿顿都要精打细算才能撑到新粮下来。每人一年分十来斤带皮麦子,送到磨坊磨成面粉,又轻了不少。平时粪坑里都是清一色的黄色。一旦有外村人挑担子来卖新鲜菠菜,粪坑里才会突现一坨坨新绿。
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农民,但是在新中国最苦的还是农民。三年大饥荒中城市的粮食副食供应很差,连蔬菜都是限量供应。妈妈由于饥饿双腿浮肿。我跟别的孩子到胡同西口《天源酱园》厂的垃圾堆拣做酱菜的下脚料回家补充菜食,在后院大槐树开始飘香的时候用带钩的竹竿采摘槐花拌玉米面蒸食。但是北京市区很少有人饿死,几千万人口饿死大多发生在农村。
到1970年,罗庄交过公粮以后分给农民的口粮不够糊口。家里孩子多的分到的口粮多一些,全家搭配着尚可度日。单身汉一个人分的口粮不够吃,他们或者给相好的人家帮忙,然后搭伙吃饭,或者半年劳动、半年到内蒙流浪讨饭。即便这样,还不断有人到农村查账,看有没有瞒产私分。
我不明白村里怎么那么多光棍汉。姐姐们说,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又舍不得花灯油钱,天黑了两口子干嘛?地方穷又没有计划生育措施,家里生了男孩养不起也舍不得丢掉,常常有女孩生下来就被溺亡。失去女儿的母亲可以做奶妈一个月挣10元钱,顶一个壮劳力在地里干几个月。这让我想起了北京大兴县的红星奶牛场,养公牛消耗饲料不划算,往往把牛犊处理掉,独占母牛的乳汁,都是经济驱使的选择和无奈。长年下来,罗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少男人成年后娶不上媳妇,幸运的西渡黄河娶个陕北姑娘过来。陕北生活更加穷困,让人难以想象。
虽然农业学大寨已经多年,我看到的罗庄还是一个穷乡僻壤。村舍大多是用土坯旋的窑,木料用得极少。纸糊的窗扉,留一个小小的玻璃窗透亮。盐碱地产量低,分给各家的自留地很少,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发展副业和农贸。光靠大田里的收成难以维持村民生活,卯足了劲儿也刨不出足够的吃食。村里村外树木不多,光秃秃的主干上树冠很少。我当那是什么特殊树种,知青告诉我,枝叶被村民砍去烧饭暖炕了。虽然山西盛产煤炭,但是农民买不起煤,主要还是使用秸秆柴禾。
俗话说“虱子多了不怕咬”,来到雁北的穷乡僻壤,知道干了活儿也挣不到钱,还要倒贴钱,知青也就别想钱了。每天踏踏实实干活儿,有饭吃,有朋友相佐,就好了。
村里的老百姓虽然不富裕,日子照样过。村里的女人依照古风,把发际线刮剪得整整齐齐,自有一番风韵。她们笑话这些北京女青年没有清脸修鬓的习惯,不好看。
1970年夏天第一次到罗庄看望姐姐时,老乡闻讯纷纷跑来围观知青的客人。他们看我的蒙古袍,试我的蒙古靴,评价我被风吹日晒染就的黑脸,热闹了好一阵子。如今我到罗庄插队,感到村民看我的眼光总带着审视和新鲜感,估计还有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我这个偏于自由野性的牧牛人在老乡异样的目光下开始腼腆收敛。
罗庄知青
锡林格勒大草原地广人稀,知青大多分散住到牧民家里放牧,难免有孤独感。知青初到罗庄时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然后自己打土坯,在老乡的帮助下建好知青点儿。知青住的窑坐北朝南,一溜十二间分成四套,每套一间堂屋加两侧的卧室。知青们不习惯睡北方农村的土炕,窑里一直支着简单的木板床。盖窑的钱来自国家发放的知青安置费。做床板和床凳的木头和窗扉上的玻璃还是知青从北京买了运到罗庄的。
山阴县安排了具有体育特长的知青到县城的一些工厂工作。我到罗庄插队时姐姐户口在罗庄,人在县大修厂做学徒工,兼县里中学的排球教练。我就用她留在罗庄的床铺,和储立新、张祖和同屋。姐姐不在身边,校友们都像大姐姐一样帮助我,减少了我初到时的很多困难。在寂寞的草原上我是独来独往的女强人;在罗庄,知青们的亲情柔化着我,我享受了被关爱的温馨。
夏天在牧区我们取用河泡子水,里面不乏牲畜的排泄物。冬天用雪水,在锅里化开后捞掉混杂的枯草马粪。现在在农区用上井水,至少刷牙洗脸有了洁净水,卫生条件好很多。
我们的堂屋里有个大水缸,洗漱用水要到水井去挑。储立新经常主动去挑水。看她大步流星地挑水走路我很佩服,也练习挑水。罗庄的水井不深,村民用扁担的钩子钩上铁桶,在井里晃荡打上水,再用扁担拉上地面。我第一次自己去打水,铁桶就脱钩掉进了水井,让我十分狼狈。我急忙跑回家求助,张祖和安慰我说这样的事他们初来时也经历过。她找了个老乡,三下五除二就把水桶捞了上来。以后我每次打水都格外小心,生怕水桶再掉到井里。
在内蒙家家都有装水的椭圆形大木水箱——台娄,运水都用牛车。现在挑水用扁担,压在后肩,把脖子上的筋都扯得生疼。路过的村民驻足微笑着看我担水,像看村里新来的戏班子。一旦有什么彩头,便是饭桌上的一道小菜。我忍着肩膀的疼痛,右手扶着扁担,左手甩开,让两端的水桶随着脚步颤悠着,尽量走得自然潇洒。既然有观众,这台步就不能走乱了,留下笑柄。
早上出工前大家在村里集合听队长分配任务,然后各自拿上适用的农具到指定的地块劳动。我在罗庄没有任何农具,但是从来没有发愁过,苏燕燕和张祖和会给我找到农具。如果知青点儿没有,就去老乡家借。
一次苏燕燕去老乡家帮我借平头铁锹,一进院门就看到屋里女人在窗前向她焦急地摆手不让靠近。她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继续往里走,家里的男人拿着剪刀冲了出来,追着要剪她的裤脚。苏燕燕吓得飞跑回来,躲过一劫。当地的村民在家里有人坐月子的时候,会把布条系在院门的门框上,阻止外人进入。苏燕燕没有注意到标志冒犯了风俗,当家的跑出来剪裤脚是辟邪的补救方式。
牧区放牛靠的是骑马圈赶,男女体力的差距没有多大关系。农业劳动可是要凭力气,有些还需要技术。我们锄玉米,一垅地望不到尽头,一早到地边,锄一个来回就到晌午了。我们和村民一起排成一大溜向前走,一人占一垅地,负责左右两垅苗。一窝玉米苗有两三棵,挤得很近,我们要在每一窝里保留一棵壮苗,锄掉其余的苗。除了间苗,还要保墒,把周围的土锄松。我的锄头下去没个准头,不是锄不到想要锄掉的苗,就是把一窝玉米连锅端。眼看大家跑到前面,我手忙脚乱跟不上,心里十分着急。
储立新和郑丽娜在我左右两个田垅锄地。她们把我夹在中间,顺手帮我把左右边的玉米苗间好。我只要把垅间的土锄松,就跟着她们往前跑。锄到地头,可以望见桑干河了,那些干得快的壮劳力早已坐在地头抽了一袋烟。我们没有停歇的时间,就又跟着他们换了田垅往回跑。一天下来腰酸臂痛,体会到了农业劳动的强度和自己的笨拙。除了知青,参加锄地的农民里没有妇女。我真佩服这些姐姐们,两年里她们从窈窕淑女锻炼成健壮的农民,扛起了半边天。我能够应付最初的农业劳动全靠她们的帮助。农活比放牧累,但是一帮人一起干活,说说笑笑,还是热闹得多。
知青除了参加劳动,也积极为改变地区的落后面貌出谋划策。雁北干旱,盐碱随着水分的蒸发升到地表,影响收成。看到村边流淌千年的桑干河水,知青帮助大队筹划建造高灌站,引河水浇灌农田。知青多次跑大同到雁北专区联系求助,把变压器、电线等器材托运到东榆林火车站,再肩挑手抬搬回罗庄。他们买水泥电线杆,架电线,把电引过桑干河,终于让罗庄在1971年秋季通了电。我在罗庄时也到高灌站劳动过,领工的是知青杨百揆。
半个世纪过去了,知青帮助策划和参与修建的高灌站还在浇灌着罗庄的田地,有效地压制了盐碱,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让罗庄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山阴县目前划归朔州地区,罗庄的高灌站目前是朔州最大最重要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列入国家的末级渠系水利工程,里面有知青们的功劳。
只靠农业生产不能让农民摆脱贫困,村里派出民工参加国家的基建项目以增加集体收入。我曾经跟着民工大队去修公路,那也是一段特别的经历。
大队承包了一段新修公路的碎石工程,国家支付民工每人每天一角一分。虽然支付极低,但仍然是村里一笔额外的现金收入。我戴上草帽,拿个大榔头就跟着大伙儿出发了。步行几里地到达工地,坐在地上把拳头大的石头敲碎,达到铺路的标准。
这是个出力气就行的活儿。我快快抡锤击石,手臂震得发麻,石头一个个被敲碎了。旁边的知青压低嗓音对我说:“慢点儿干。”我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她,她告诉我:“干完了就没有钱了。”我扫看周围的村民,都是不慌不忙地聊着天,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慢慢地敲碎。我立刻感到农区和牧区人们心态的不同,理解了为什么说蒙人没有汉人精明。
在锡林格勒大草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烟的稀少让蒙古牧民之间无私的互助成为了必然。畜牧业带来的收入让他们没有对基本生活的担忧。在广阔的草原上他们心胸开阔,自由奔放。而在雁北贫瘠的土地上,经过了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村民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对于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挣到8分钱的村子,一天有一角一分的民工支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路修完了,这个财源就断了。存在决定意识,生存的需求增进了农民的“智慧”。如果把计时支付改成计件包工,公路的修建可能会快很多。
我在村里参加农业劳动,和老乡打交道的事全由校友姐姐们代劳,所以罗庄村民对我来说始终是个模糊的整体,没有哪一个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老乡那里,我的名字始终是“董盈的妹子”。他们对我的记忆,停留在1970年夏天我出现在罗庄时对他们的视觉冲击。他们总忘不了我黢黑的脸,身上的蒙古袍和那双放在堂屋地上、每个人都要试穿一下的蒙古马靴。我这个“外星人”生活在罗庄,一直得到乡亲们更多的包容。
在罗庄最轻松愉快的时候是晚饭后和同屋的张祖和、储立新走出村子,坐在地头田埂上乘凉。骄阳退去,塞外吹来的风带来丝丝清爽。面前是漆黑寂静的原野,萤火虫的光亮星星点点,时明时灭。脚下水渠的细流静静滑过,倾听着我们的高谈阔论和窃窃私语。我们诉说着插队的经历和各地的世态民俗。她们最感兴趣的是我的内蒙经历。当我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塞外风情和草原上的奇闻趣事时,感觉到她们惊异的眼神,听到她们哈哈的笑声,心里自有几分得意。锡盟草原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浪漫的、荒蛮的。一切艰苦过去,脑海里留下的是探索者奇特美好的记忆。
我们聊过去,聊现在,却不谈将来。将来永远是隐秘在苍茫之中的未知。就像桑干河底的一个沙粒,是随波涛流入永定河,再奔向大海,还是在什么地方沉积下来,成就千年后的岩石,不得而知,它只享受今天河水的冲刷洗涤。一天劳动过后,一群情窦初开的北京大姑娘聚在雁北的田野上分享人生的经验,探索生命的奥秘,苦累都抛在了脑后,我在罗庄的生活并不寂寞。
——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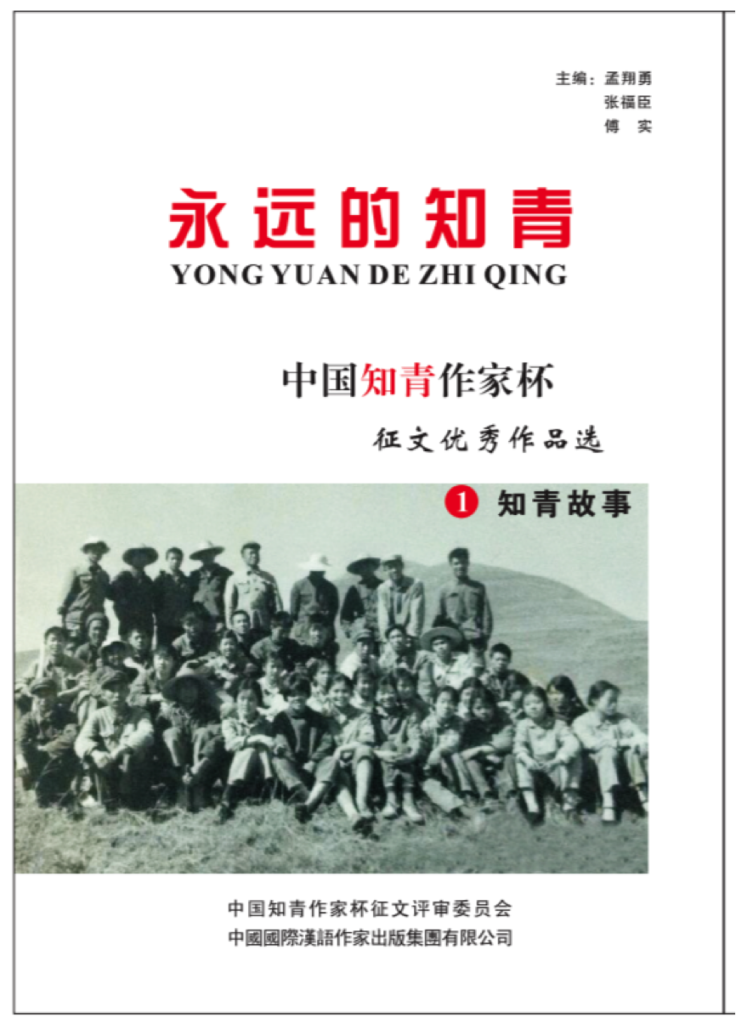
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