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道工到大学生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大鸣
作者近照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下班回家。那天,与往常不同的是我大姐先到家,在门口迎着我,脸上放着光彩。还没等我停好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她就大声朝我说,“要高考了,考试可以上大学了!”
“什么,什么,你在说什么?”
大姐见我脸上一片茫然,语气放平缓了些:“高考制度恢复了,不用推荐,只要考试,按分数择优录取上大学了。”
“是吗?那太好了,这下大姐终于能上大学了。”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她由于学习成绩好、工作出色曾被工作单位选拔、推荐上一所中专医校,但在最后一关却被领导的亲属给顶下来了。
“大鸣,你也要考大学!”
“我?高中没上,考啥呀?”这两年当煤矿铁路轨道工的经历顿时历历在目⋯⋯
上学梦断,成为铁道工
“文革”期间,我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大兴安岭的“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那时,父亲的工资停发,做护士的母亲靠着她一人微薄的收入维持我们姐弟四人加上奶奶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母亲承担着生活上的困苦,更为压抑的是戴着一个“反革命家属”的黑帽子,见人抬不起头。由此积劳成疾,我的母亲得了胃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三个月后就撒手离开了我们这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年仅三十七岁。那年,我十一岁。
我的家乡黑龙江省鹤岗是一座煤矿城市,八大煤矿中,七个深井煤矿,一个露天煤矿。市就是矿,矿就是市,其它都是附属单位。井下事故频发,矿工安全没有保障。那年代,中学毕业后,不是上山下乡,就是下井采煤。当我不足十六岁时,那个露天煤矿招工,正好有个“顶替接班”的机会,我家可有一子女用我母亲的公职名额参加工作。父亲为了让我留在身边,也不用在高中毕业后去极为危险的井下工作,就给我报了名。这样,我告别了同学和心爱的学校,穿上肥大的工装,当上了一名露天煤矿的铁路轨道工。从那时起,每天早上我骑车上班与学生上学同路。望着曾经的同班同学们肩上挎着长长带子的书包,说说笑笑地走向学校,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每当见到他们,我就赶紧加快蹬车,低着头从他们身边冲过。
在煤层不是很深的地质环境里,露天开采是更为经济的采煤方式。在旷野中,用电铲挖掘机把岩石一层层剥离运走后,再用同样的方式将煤炭挖掘运到地面。“七分岩、一分煤”,那是说我们多数时间在搬运岩石。不停修建的矿山铁路就是为了运岩石。地处东北边陲的鹤岗煤矿,到了冬天,真可谓“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温在白天常会降到零下三十几度。在山顶铁路的边沿,呼啸的寒风夹带着丝丝的口哨声,能吹透军用“大头鞋”、羊皮大衣和狗皮帽子。
矿山轨道工的主要工作是抬铁轨,扛枕木,打道钉。我那时身体单薄,一个人扛不动枕木,八个人抬铁轨,工长一声号响,七个人站起来,我一个人趴下了。那些工友大叔和大哥们倒还体贴我这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别碍事了,你就拿着篮子捡道钉算啦。”那段时间,我跟着工友学会了抽烟、煮饭,也唱会了夹带着黄段子的劳工号子。
由于我从小喜爱美术,入职不久后矿区工会一旦搞活动,就上调我到区部脱产“搞宣传”,做小报美编,刻钢板,印报纸,出黑板报。活动结束后,我再回到轨道工班组捡道钉、维修铁路。
我(后排左二)和露天矿工师傅们在一起。前排左一是教我做“红工医”的和蔼的张医生。
那些年,政治运动潮起潮落,贯彻执行向赤脚医生学习的活动,矿山要培养“红工医”,由一名医院下放到采区的医生带一名工人学医。人家看我干事不毛糙,也就让我做了半年的“红工医”,
学针灸、肌肉注射、挂吊瓶和打静点。逢年过节,又叫我参加汇演慰问,参加合唱团、化妆表演和京剧清唱。做轨道工的两年里干过几个行当,就是没做应该做的事情:上学读书。万没想到偏偏在这时,中断了十一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叫我只能望天愣神了。
一战而捷,我却决定放弃
“大鸣,你没上高中,但你的初中底子好,考个好中专一定不在话下!” 曾经和我最要好的几位同学一致给我出这个主意。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回家将这事还没跟我大姐讲完,她就打断了我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大鸣啊,要么你不考,要考就考大学!”我就更急了,带着哭腔说:“可我断了学业,没上高中啊!”大姐眼里闪着坚定的目光,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来教你,你能赶上!”
自宣布恢复高考制度起,每个年轻人、每个家庭、整个社会都为这突来的喜讯沸腾了。“响应党的号召,勇敢地站出来,接受祖国的选拔”是当年的时代最强音。不再靠关系、走后门儿,靠才华和能力进大学,改变我们命运的时刻来到了!也就是大姐一锤定音起,我开始磨刀擦枪地开始备战了。白天还得照常上班,到了晚上,我捡起了生疏的课本,大姐成了我的数理化老师。
“往这儿看,这就好比三角函数的四个象限,逆时针转动,一、二、三、四。”大姐指着装有四块玻璃的门窗给我讲解着。从元素周期表到化学物质的酸碱性,从牛顿力学定律到物质的状态转变,两年制的高中课本,用了一个月的晚上,稀里呼噜的吞下去后,就进了初考的考场。
我和我的大姐
本来抱的希望不大,没啥负担,倒是一路追杀,考过了初考进终考,居然被大学录取了!那天,我初中时最要好的伙伴像古希腊的菲立比斯从马拉松长跑到雅典传报胜利的喜讯一样,气喘吁吁跑了五、六公里来到我工作的矿上,将通知的电报交到了我的手中。我的心狂跳了一阵,颤抖着双手打开电报一看,心里立刻就凉下来了:“你拟被录取到东北林学院林区道路工程专业,如接受录取,请回电。” 我的天,我报的是建筑学专业,怎么,这是要让我到深山修路去啊!没什么好多想的,反正再有四个多月78级的初考也就开始了,既然一个月读完高中考上大学,我再用四个月去好好复习,一定考上重点大学,上我梦寐已求的建筑学专业!这人哪,出了点彩,就忘形了。
破釜沉舟,孤军再战
送走77级入学的大姐,又重新开始高考复习。没有了辅导我的大姐在身边,这次可全靠自学了。依然是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家里每日只有上初中的弟弟陪伴,还帮我做饭。那几个月里,目标是要将刚刚粗略学过的高中课程深入理解,订复习计划,掌握进度,解答难题。没有人引路,没有人指导,一切全靠自己。高考赋予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独自承受的锻炼和考验。
78年初考过去了, 成绩还好。正当雄心勃勃迎接首次全国统考时,矿区党委书记对应考员工讲话了:“你们不能总想着考试啊,还有工作要做的,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考不上就回矿好好上班,安心做矿工吧!”不偏不倚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书记给这些年轻人交出底牌了。没上高中,考上大学又放弃录取,巨大的压力袭来。家里没有父母在,就更没了底气。压力影响了心态,让我生了一场大病。这样,带着最低潮状态的我进了统考的考场。打开数学考卷,眼前一阵晕眩:一道题也不会!重新看一遍,还是不会!当时都有了撕卷破门而出的想法。“考不上,就回矿好好上班,安心做矿工吧!安心做矿工吧!”区委书记的语音在我的耳畔轰鸣,一旦出了这个考门,就永远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了。咬紧牙关,再往下看,从那2分的题目做起⋯⋯
不肯放弃,不懈的拼搏,坚持考完一门又一门的课程,我最终获得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佳木斯农业机械学院(现佳木斯大学),焊接技术与设备专业。学院虽小却依然给了我上大学学习的机会。我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我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焊接学科奠基人之一田锡唐教授的研究生。同时由国家教委公派、英国政府提供中英技术协作奖学金资助,经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进行了十个月的英语培训、考试,于1986年秋赴英留学读博,这都成了后事。
回首往事,辍学高中后的那两年半在社会历练的日子,与当时文革后期在学校的“虚度”相比,更丰富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搞美术教我观察世界,登台演出锻炼我表达的能力,学习护工实际体会关爱的含义,而劳苦的工作让我在生活中感恩。那两次的高考经历锻炼了我在关键时刻迎接挑战、独立进取的能力,也磨练了不甘失败的意志。四十年前那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高考制度的恢复,也完全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我在从轨道工到大学生那特定历史背景下所获得的,为我以后的成长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对我一生中产生的影响,无论怎么说,可能都不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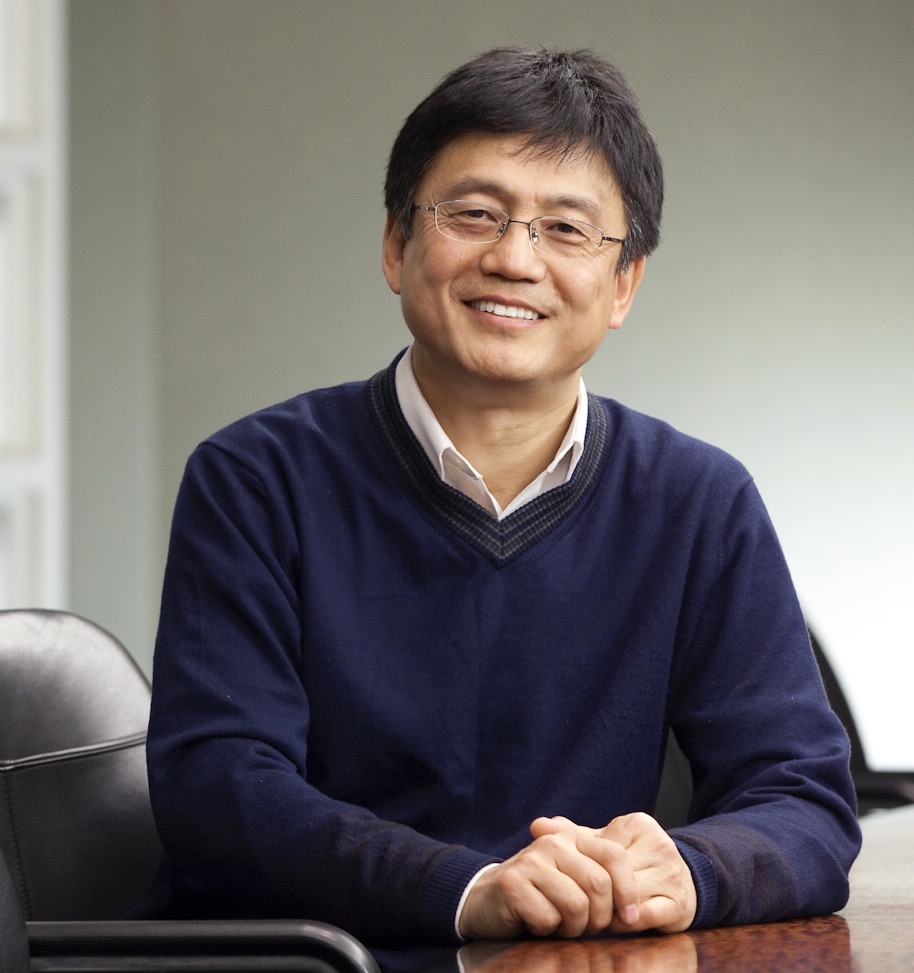


0 评论